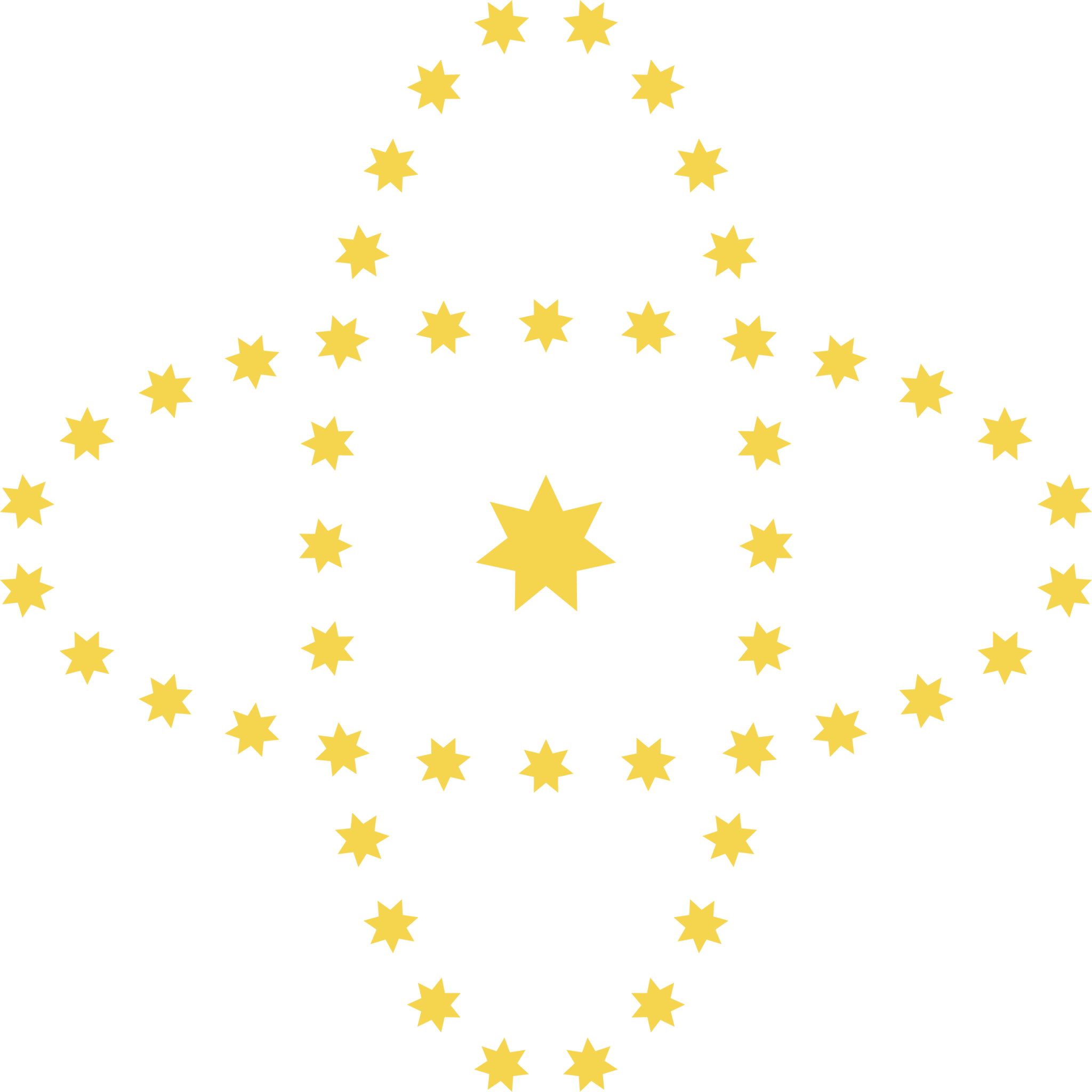撰稿:仰望星空
我从小到大在中共国的经历,每一个似乎被遗忘的点滴,都因爆料革命而重新串联起来,成为了我独特的个人经历写照。
我的幼儿时期,在班上连个上舞台的机会都没有,却被父亲教会了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学生时期,我讨厌背诵政治课的条条框框,但课本上一句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带动另一部分人,最终走向共同富裕 ”让我心驰神往了好久。但初三那年,每天骑车路过一拆迁房,看到一位穷困潦倒的老父亲,用板车拉着智障的女儿,期间我和同学商量要给父女俩送些钱,等到拆迁房处盖起大楼后,父女俩也消失了,他们从此只出现在我的回忆里。我也不断寻思着,那部分富起来的人在哪里?为什么没有人帮助穷人?
参加金融工作后,我没有家庭背景,也没有蓝金黄的能力,完成不了银行的拉存款任务,拖部门后腿,但所幸从来没被拉入过领导宴请存款大户或外领导的宴席桌,只感觉各种陪,陪吃、陪喝、陪唱、陪跳是件恶心的事。曾经有在体制内当领导的亲戚,要给我面授往上爬的秘诀,在家宴酒上教我敬酒,还得有能喝下半瓶红葡萄酒的能力,顿时不想再碰酒。

图|图片来自网络
当过好多回伴娘后,心中默默立下心愿,不摆做给人看的婚宴:婚宴俨然成了一个显示你的身份、地位、财富、人脉的竞技场,在一个戴着有色眼镜的社会里,我不愿去触碰这条敏感线。
一路上与假和虚为伴,我每天祈求上天给我一个机会,能逃离中(共)国。终于有一天上天安排让我的先生从千里之外的瑞典,发来给我一封电子邮件,随后更飞到了中国来看我,于是我的出国之路和成家之路都变得顺理成章。出国对我来说,就是把墙内那一页纸翻过去了,我只面对我的新生活,新语言,新文化。我从不花时间去看社交媒体,如油管,脸书,推特等等,唯有留了个微信与国内亲戚联系。
记得在中共国,我有一个排解忧愁的最佳方式就是坐在一高处,享受与天空星辰云朵独处的时刻,很多现实的说教与矛盾,及无法与人沟通的想法,唯有仰头目视那片天空,我才能抛开烦恼,感到愉悦。日后参加爆料革命,仰望星空就成了我的名字。
病毒的出现,让我认识了爆料革命和郭先生,并下定决心加入爆料革命和农场
认识郭先生和爆料革命,我有两个领路人,一个是起间接作用的瑞典老人。2020年夏天我与这位老人见面谈论当时疫情时,他提到了西方社会及媒体的左倾及病毒的来源。这与我对当时中外截然不同的防疫政策所引发的疑问,质疑西方故意把整个社会拉下了病毒的深渊的想法,似乎走在了一个频率上。一回家我就找油管看,当时不慎还是找了好多伪类的油管视频,如江峰时刻,明镜,通过这些节目,与我作为一个墙内出来的小百姓来说,那是符合我的常识的,但我当时没有能力分辨出他们的伪。
看了一段时间后,我就找了在墙内的老同事聊天,这一聊,她直接就跟我说去找郭文贵和路德的视频看。这一看就一发不可收拾,当时我看路德的节目比文贵先生的多,因为每天上下午的更新,觉得很过瘾。听路德的节目,一般很少提及农场及各项G投资的事,加上当年是我入瑞典大学的第一年,学业非常繁忙,加上要照顾家庭和小孩,就没有时间顾及其它新的事物,对爆料革命只能停留在收听的层面。
但通过文贵先生的视频,我听到了更多的关于农场及战友保命保财的更多与自己息息相关的信息,爆料革命对我的吸引力和对文贵先生的信任感与崇敬,是我这一生都从未感受过的,我开始萌生要入爆料革命队伍的想法。
2021年我加入了“德农”,不幸又是中共安排的一堆伪类和特务渗透的地方。之后,我非常有幸地转入了“澳喜”,参加了小皮匠带领的多语组工作。自从来到瑞典生活,我作为一个不过问政治,每天只管自己一个小家的小百姓,如果不是中共实验室病毒出来,如果不是吃人血馒头的伪类们天天坐着骂共产党,如果不是有这么个所谓勤劳的路大脑袋每天早晚坚持作节目,我怎么能有契机发现真正的宝藏和真正灭共的七哥和爆料革命呢。这一路走来,我发现这中共真是不作不死,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而也正是郭文贵先生领导的爆料革命,给我心中多年积攒的疑问与困惑作了最充分详实的解答。我突然想起了我将近二十来年的努力争取机会出国,正是为了多年后能遇上文贵先生和爆料革命,对于超音速地接纳爆料革命和灭共理念,也算是厚积薄发了。
过去墙内生活经历和感受(假,丑,恶)(蓝**-恶,金–假,黄-**丑)
七哥直播中说的中共对世界的蓝金黄,我听了以后,觉得一点也不陌生,中(共)国社会不就是一个被蓝金黄的工厂嘛,感觉这一样的配方不仅用在七星级饭店里,同样也被用在小饭馆小食堂里。
先说“蓝”,对于从未踏出中共国监狱的人来说,当被湮没在错误虚假信息里时,是不会感到窒息的,因为总有贬人褒己的信息,贬人指贬低西方,褒己指歌颂中共国治国方针,让大家误以为自己生活在美好的世界里。零星冒出的一些真实的声音,我们只当成了耳边风。记得有一回我在单位办公室里,传真机自动接收到了来自大纪元的通讯,是些关于法轮功、江泽民和反共的言论。我当时独自在办公室里,看了以后随手把纸揉成团扔垃圾桶里了,也没有与人讨论过这个事情。现在回想起来,也有可能是国安在利用大纪元,审查墙内人的政治觉悟,因为现在知道大纪元早已被中共拿下了。且当时据小道消息,我当时的办公室主任还有个暗差,他在国家安全局里是有编制的。
再一个例子,是单位一同事去北欧旅游,回来后告诉我们,她在挪威时看到新闻,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被颁给了中国人刘晓波,在国内新闻相关信息一个字都找不到,她当时说起来还是有点愤愤的,但我们整个办公室的人听了以后,也几乎没有任何反应,倒不是不敢言论,而是我们对自由和民主的边儿都没嗅到过,也不知它长什么样,能发出什么样的评论呢。也就是这位同事,因为每年都出国度假,回来时不免也要翻墙听听国外的声音,当我两年前和她说起郭文贵时,她马上反驳说,郭文贵不可信,她其实翻了墙也没逃出中共布下的九层妖网。中共对网络的控制,其手段的险恶,是常人无法想象的。
说到“金”,哪一个企事业单位不需要这个啊。以我在金融系统从业的经历为例,员工的效益奖金就是和存款任务挂钩的,拉存款时,号召员工要奉献,实则就是要员工去努力攀有金库的主,情商高是被用在如何挖掘对方有什么样的需求,如何在宴请金主的饭局里让对方舒服,给对方送财,如何编织一张对自己有利的人际关系网,没有钱搞不定的事。不管以什么手段,拉到存款,那么本人的职位也随着业绩而高升。有了金的驱使,作假也就成了水道渠成的事了。比如,奖金发多了,会被税务部门盯上,于是有了全员消费后要发票的举动。比如我今天买了衣服,鞋子,吃了顿饭,统统要开发票,单位发奖金时,按奖金数贴发票。要知道在一个法制健全的社会里,这种行为叫偷税,是犯法的,而我们全然不知。直到多年后,一个瑞典人跟着自己的中国女朋友到中国旅游,在与友人的饭局后,瑞典人看到自己女朋友付款后,不把发票留给自己,而是交给了开工厂的朋友后,他生气地指责自己的女朋友,作为一个从事过财务工作的人,这点法律意识都没有,帮助别人偷税,而这个中国人听了以后也只是哼哼一笑,笑人家不懂国情。我听了这段故事后,才感慨中共治下的中国人,真是全民皆罪啊,但有几人会懂呢?
“黄”就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佐料了,什么银行行长啊,高管啊,有几个部下美女当情人哪,外面有个私生子女的,那都不稀奇了,没有才不正常哩。中南坑那班老杂毛和他们的白手套们在高级会所的密室里玩弄女人,这上梁不正,还怕下梁不歪?这些人深谙人走茶凉的社会运作规律,在退休前更要疯狂地来一把。曾经就有单位的好姐妹讲述过自己怎么巧妙地躲过领导的性骚扰的亲身经历。另外我有个亲戚是做车辆保险的,曾经就被保险公司老总要求当小三儿,但我这个亲戚是个正直的人,她当机立断说,我拉来的保险,给你提成,就那事儿我不干,这才免除她被咸猪手沾污。这种丑陋的肮脏事儿,就像中共国的地沟油一样,到处都是。
这几年的心得感悟
关于尊重的真谛(在中共国,我们只做到了像小孩一样的呀呀学语式的尊重(表面工夫);真正地做到尊重,需要深刻地了解人性,了解世界,学会尊重,这是一个过程)
关于尊重,这个看似很基本的普世观,在受到外来文化和不寻常事物的碰撞时,我发现我们中国人普遍不懂得什么叫尊重。第一回受到冲击是,我的瑞典老公第一次和我见面时,竟问我,我家长辈亲戚的名字,我好生奇怪,你怎么可以问长辈的名字呢。后来我来到瑞典生活后,管所有长辈直呼其名,让我一度非常不适应。从小的中共教育背景,几乎把尊称与尊重划上了等号,我们只做了尊重的表面工夫,尊重的深层含义,在中共国的生活中层层被剥离掉了。比如在单位里,很少看到有不尊重领导的,但梳理下关系后,发现那不叫尊重,那只是畏惧人家的权势,你的饭碗得靠着人家给;但在家庭生活中,因从小的养育与被养育的天然关系,使得日后双方的手都伸得太长,没有了空间,子女成了父母的附属,父母成了子女的包办或者伽锁,两者间的尊重也不复存在了。
来到西方后,突然不需对上级权势畏惧了,父母的管束没了,发现自己也失重了,特别是两年多来的疫情,因我个人的特质,与爆料革命能走到一个频率上,坚信疫苗是有毒的,但西方人,与我们的生活轨迹与背景完全不一样,我没有尝试以他人的视觉去看待问题,反而像上级一样义正言辞地警告对方疫苗有毒,但这一招没有吓住对方,然后就像父母一样,以爱的名义劝对方不要施打疫苗,再后来发展到愤愤不相往来。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这个例子很特殊,但我这样的行为,其实又回到了中共国,试图以一种强硬的声音去覆盖别人的声音,而不去聆听对方声音,与对方形成有效沟通。因为不懂得如何尊重对方,而采取咄咄逼人的方式劝导,不仅没有阻止别人打苗,反而失去了与对方做好朋友的机会,损兵又折将。如果能本着尊重对方有自己的见解,然后像对待婴儿一样,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评估对方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和承受能力,有效地搭起一座能承载的桥梁,即使没能成功劝阻他人打疫苗,人性的关怀与爱还是可以连接彼此。
关于尊重,还要提个小事。19年那会儿,中共国的媒体里有传出小朋友在幼儿园里被性侵的事,我从一律师朋友的微信里了解到,他们的孩子入园后,都有摄像头安在园内各个角落,家长一边上班,一边还可以观察小孩的一举一动,他们觉得安心了。那时候我就在我的小孩入园时,向园长提了这么一个建议,立马被另一瑞典小孩的家长反驳掉了,她说我不需要知道小孩的每一举一动,我要让他保持他自己的空间,我要保护他的隐私。我当时一愣,还没缓过来,可现在想想,尊重已经一再被其他看似合理的理由给践踏得体无完肤了。更是自已感到羞愧,活了快半辈子了,根本没整明白什么是尊重。
逃离了中共这座大监狱,我们有了自由的空间,去学习如何尊重他人,不管他是小孩,老人,不管他是家里人,还是外人,不管他是本族人,外族人,在不同的状况下,表现肯定不一样,但我想宗旨应该是能换位思考,允许有不同的声音,允许别人有自己的选择。多多去了解这个世界,也能帮助自己学习尊重他人。
总结与呼吁
在此我要对还不相信爆料革命的墙内墙外的中国人说一段话,希望能作深入思考。半年前一位在德国的发小,发了奇葩说讨论的一个话题给我:法国卢浮宫里失火了,一幅名画和一只小猫,你先救哪个?她的观点是不要把自己当成救世主,可以主动选择救画还是救猫,在现实世界中,我们都只是那幅画,或者那只猫。由这段辩论话题,她引用了微信中有人发表的“疫情三年,我学会了闭嘴”的文章。这言下之意,与墙内亲人说的一样,劝人不要关心政治,你没有这个能力改变。
我回了她一段,在这里画和猫都不是问题,而是谁烧的那把火的问题。也正如七哥当年给穷乡僻壤捐款,捐了那么多,穷人变富了吗?根源在哪?在共产党,现在共产党把这把火烧到全世界了,还争论先救哪,有意义吗?中国人在墙内当井底之蛙,出墙了,还背井离乡,中国人什么时候能挣脱出这口井?现状是中共把带有火苗的木条往井里扔,中国人该怎么办?
最后,我聊一段我的奇特人生轨迹:我曾经就读过的幼儿园和学校,全部都在我离开后不久,不是没了,就是变相地成为了别的学校,总之那个名就不复存在了,参加工作后,我只做过一家银行的工作,朝思暮想地就想出国,离开中共国后,我有时会静下来想,按我的人生轨迹,这家银行应该也变没了,或变成别的什么银行了,但看起来还是好好的呀。直到入了爆料革命,我才想明白原来是我狭獈了,我离开的哪儿只是一家银行啊,而对一个国家,这预示着这个国家未来起码不是以现在的名头存在,肯定也要消失。冥冥之中,天也要灭共!这也更坚定了我的灭共信念,战友们,我们的灭共事业是百分之百会成功的,没有了共产党,才会有新中国!
作者:仰望星空
编辑发布:小湫
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平台不承担任何法律风险。